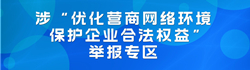三烈士故居纪事(下)
瓦埠暴动
瓦埠暴动是在1931年3月。其时,我已经在上奠寺小学上学。这次暴动,在寿县历史上是件大事,可是我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天下午,小甸集的曹克科和曹竞两位来到家里找二伯有急事,这两位都有特点让人很容易记住:曹克科留了两撇八字胡须,背后人们都叫他仁丹胡子;曹竞人称狗老爷。我总觉得他们滑稽、很好玩。所以他们和二伯说话,我不愿意离开。只听他们在谈论瓦埠暴动,说曹鼎带的队伍被国民党县队、联庄会的队伍(地方武装)包围在张嘴子,要组织人、枪去救他们,来找二伯商量办法,他们紧张地谈论了一阵子急速离开。这就是以伪装“小甸集联庄会”队伍的名义,占据了有利地形,掩护曹鼎突围成功的行动。三岗的曹维邦等人参与了这次行动。
瓦埠暴动失败了,但它教育了革命者,教育了人民,从此寿县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篇章。
启蒙教育
我上的小学是寿县县立上奠寺小学。按习惯我应该在小甸集上小学,因为这里是曹姓户族的中心。由于曹云露奉命到上奠寺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因此我和云青以及村内几位少儿一起,都到了上奠小学读书。
曹云露平时在学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和我们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我们讲解富人为什么这么富,穷人为什么这样穷,剥削、阶级、压迫等等。进而讲到地主、老财、官府、国民党是一家,天下穷人是一家,应该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云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是那样耐心,循循善诱,有时甚至和我们一起背诵古人“六月禾未秀,官中已修仓”这类诗词,并为我们讲解。
少年时期接受的印象最深的教育,是针对性的教导。我上小学时,家中已经告诉我父亲曹渊牺牲的情况,而且村中长辈们见到我多要鼓励几句,好好学习,长大了替父亲报仇啊!中国历史上替父报仇的如伍子胥等英雄人物也进入了我的脑海,曹云露察觉了这些情况,针对替父报仇这种思想,他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报私仇,我们要推翻整个旧的社会制度,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广大人民求解放,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的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富强的新社会。三叔(指曹渊)就是为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啊!为了个人报私仇,这种思想岂不是太渺小了吗?这次谈话,开阔了我的思想境界,为我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奠定了基础。
曹云露在学校当了三四个学期的教员,瓦埠暴动后奉命离开,专门从事武装斗争活动。1931年水灾,紧接着是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土匪四起,游击队活跃,军队“进剿”,街上常常驻扎有国民党的部队,街头有几次挂起了人头示众,说是被捕杀的共产党人,可是街上的人说不是,是被地主、老财陷害的农民。往往在路边也碰上被杀害人的尸体,至于是什么人,就无人能回答了。由于土匪骚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学校两次被迫停课,一次是我们这个班全部迁到乡下上课。一次停学无法复课,我们几个同学只好转到私塾先生那里学习。在这些变动中,每一次变化,我都接触一次新环境,增长一次新知识。这一时期使我感兴趣的,还是放学回到家里和潜藏在家里的游击队员们谈论的一切。他们对我的教育和教给我的社会知识,是我终身难忘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游击队员们多是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教的歌是自编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歌曲,针对性很强,是自我教育,也是游击武装政治工作的内容。有些歌词至今我尚可背诵几句。如:
姐姐妹妹听我言莫呀,
听我言莫呀,
我们妇女真可怜
你可知道?
自从娘胎生下地莫啊,
生下地莫呀,
看是那丫头就生报,
捂死掉她!
……
除了歌曲,更多的是讲解革命道理,很多时候是我在提问。放学回家到这里来的是曹云青,他比我大两岁,提的问题往往比我深,所涉及的内容大致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地主、老财;社会主义是用拖拉机耕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劳动没得吃;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各尽其能,各取所值;共产主义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和游击队员们在一起是十分快活的,只是必须严守秘密。这是我们家庭的第一条戒律。当然还要做些我能做的事情,除了为伤员送水送饭等力所能及的活,我往往还被派出去送信、到邻村找人等。我看到的难事,常是为伤员请医生看病,政治上靠得住的医生往往来不了,来得了的医生靠不住,当然这些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可是为伤员买药常常派到我们头上,这些药物也不是什么药店都可以去买的,只能到可靠的药店里去买。有一次,家里让我去买桑皮纸,这是一般的商品,竟引起商店老板的猜疑。中医治枪伤用的是粉状药物,把药物送进伤口深部,只能用桑皮纸,当我向商店老板要桑皮纸时,老板以怀疑的眼色看着我问:“哈!小鬼,你家里要买田写地契啦?”这分明是在诈我。我当即回答:“我的灯笼破了,糊起灯笼防止夜里摔跤。”这次让我捏了一把汗,实在有些后怕。
千钧一发
瓦埠暴动失败后,由于南京国民党武装的到来,寿县党组织组建了游击大队。1931年8月,黄家坝起义失败得很惨,80多人惨遭杀害。两次失败后,寿县党组织接受了教训,改变了策略,不搞聚众暴动,采取分散秘密活动的办法,建立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抗捐、抗粮、割秋、扒粮,以壮大农会及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游击小组寻觅时机,集中起来,打击危害大的反动势力,以锻炼、发展游击武装。曹家岗一带开始成为游击健儿集合起来的出发地和出击完成任务后的休息地,游击队来往得多了,也就难以秘密了,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接踵而来。经常是游击队刚离开,国民党地主武装就来了;或者是国民党部队一走,游击队又悄然到来。
应付国民党政府的保安队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不是本地人,较难对付的是地方控制的联庄会,最难应付的、最可恨的是叛徒。国民党的保安队来了,抓不到人,在村里抓鸡摸狗,有时应付他们吃一顿饭,也就走了。地主的联庄会都是附近村庄的人,能辨别游击队员以及他们搜捕的对象,但也有其弱点可利用。一次,一位较有身份的地主带领七八条枪,从大郢孜来到园子上,显然在大郢孜没有什么收获,家中只有祖父和妇女小孩。这位地主和祖父对起话来,目的是想询问村内游击队员的情况,这当然达不到目的。这时,天色已晚,他们不想离去,对祖父说,“今晚就住在你这里,不走了。”祖父漫不经心地说:“你们的胆子不小啊,住在这里保险吗?”“住你家更楼上。”祖父沉下脸来说:“你们还是早点离开得好,现在兵荒马乱的,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能保你的险,更楼的梯子坏了,更楼也顶不了什么事。趁天色还不晚,早点走吧。”就这样连吓带哄打发他们上路了。
但也不是所来之人都可以这样被打发走的。
一次,游击队几位领导带领七八名队员来到家中,在更楼子上和后屋住下了。可是,晚饭后反动的地主武装又来了十几个人,要住下,而且为首的是敌“肃反”专员、叛徒,此人叛变后带领国民党保安队到处抓人、烧房屋,是游击队员们的死对头,家中房屋前后他都十分熟悉。他们已经走了很久的路,很疲劳,来后即声言晚上住下不走了。伯父和祖父难以让他离开,只好热情接待,在东前屋地上摆了两个地铺,安排他们住下。
看情况他们没有怀疑游击队会来到这里。可是,夜猫子进屋,绝无好心。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住在后屋的游击队员们听说“肃反”专员送上门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也是难得的消灭他们的机会,多数人主张一锅端掉,还可得到十几条枪。这可让几位领导十分为难了,命令除全体警戒外,专差两人严密监视前屋动静,然后和同志们议论打还是不打。这真是千钧一发啊!如果我们主动出击,敌无防备,全歼是有把握的,可是打了以后,血染园子上,敌人报复,不仅园子上,整个曹家岗也将被毁,这个可以掩护游击队员们的秘密场所也就没有了。而保留这个场所,对今后的发展是必需的。但眼前的情况,即使我们不出击,能否相安无事,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敌人闯进内院,战斗也将必然打响,因此所有人员要做好战斗准备。
在前屋,这些家伙白天不知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很疲劳,摆好地铺,喝了茶,就躺倒睡了。也没有留岗哨。这样麻痹大意令人难以理解。即使对祖父、伯父不存戒心,可曹云露在搞游击武装,他们是清楚的。
在后屋,游击队员们聚精会神,注视着前屋,空气似乎是凝固的,万籁俱寂。只有前屋断断续续的鼾声,点缀着这令人烦闷的夜空,这鼾声令队员们发笑,这鼾声也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
突然,围墙外树头有些摇动,发出的声音是细微的,又是清楚的,有人在上树翻墙头。这本是游击队员们黑夜进出的老路,每一位队员都十分熟悉。“坏了,‘猴子’回来了。”一位队员说。“猴子”是接受侦察敌情任务,按时回来汇报的游击队员。只见“猴子”沿着墙内的树爬了下来。人们怕他走向前屋,也不能喊住他,他不知道前屋住上了反动派,偏偏向前屋走去。
“危险!”
“做好准备,听命令!”
只见“猴子”走到前屋的窗口,向里边窥探,听到鼾声,觉得不像自己同志,不对劲,机警地退了回来,向后屋走来。同志们伸手把他拉进了屋内,“危险啊!……”就这样,又闯过了一次险关。
雷电交加风雨夜
游击队拦击打死了区长赵乘臣(人称“赵小区”),缴了区小队十几条枪,大快人心。县政府急派保安队赶来,游击健儿早已无影无踪,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大白天的行动,游击队员又都是周围村子里的熟人。第二天乡间艺人即编出了歌词,说起大鼓书来。曹家岗为首的是曹广海、曹云露,尽人皆知,参与战斗者,亦有名可指。国民党派来了兵,形势严峻,曹家岗人心惶惶,人们紧张地准备着迎接暴风雨的来临。
园子上已见不到曹云露的踪影,出事后他曾回到家里向祖父、伯父交代了两句即离开。对祖父、伯父来说,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祖父的态度还是像往常一样镇静、从容。他说这个家呀,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人最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带着两个小的先走,现在也只是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你们还要各自做好准备,等候消息,随时离家。
晚饭后,传来敌情,保安队今夜包围村庄,明早抓人。当祖父领着我和云青出门的时候,远处的云层带着闪电逼来,祖父没有理会这个,向家人交代我们可能的去向以便于联系,接过家人递来的斗笠,便上路了。
我们所走的已不是平常走的道路,而是按直线取田间小路,目的是迅速离开村庄,到达邻村。这种叫田埂的路很难走,好在祖父手里拿着拐杖,我们也只拿着仅有的两件换洗单衣,并未带什么负重的东西;远处的闪电,还不时为我们照亮着这崎岖小路。行进是艰难而缓慢的,祖父心中也是不平静的。最使祖父不平的是族内有人责骂他不正干,不去好好管教子女,而去造反闹革命,自家家破人亡,还要连累村邻。这次曹云露、曹广海带领群众杀了“赵小区”,眼见村邻又要遭殃,他自己也难逃这些责难:一方面是群众要受难,一方面是无理的责难。群众遭受苦难,使他心疼,无理的责难又使他愤怒。曹云露领导大伙儿“割秋”,你们家的子女不也是争先恐后参与进去?难道不就是“割秋”才使得“菜糊糊”碗里多了几粒粮?杀了无恶不作的“赵小区”,大快人心,你们又让我怎么去管教曹云露?还有人说,你们已经丢了一个儿子,还要丢几个?祖父说,死怕什么?他们一不偷、二不抢,死了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他们为人民谋利益,为革命打江山,牺牲了是他的光荣。看来祖父对敌人行将到来的抓、捕、烧、杀并未想论理,因为那是没有道理可论的,而族中同辈的责难却是不可忍受的。天下为什么竟有这些不懂道理的人!
事实是冷酷的,祖父以比冷酷的事实更坚硬的心,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一声天崩地塌的巨响,倾盆大雨劈头而来,风雨交加,两眼已难以睁开,双脚更难以在田埂上移动,只能紧紧抓住斗笠以抵挡狂风袭击,蹲下不动,祖孙三人靠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
周围的田里,雨水已经泛白,沟渠已可听到哗哗水声,经验告诉祖父,必须迅速离开此处,这里是冲底低处,高处的水冲下来,沟渠变河流,就跨越不过去了。祖孙三人冒着暴风雨,一步一滑,滑倒再爬起来,小心翼翼,艰难前进。终于我们跨越了沟渠,挨近了邻村。当叫开一家我叫大爷的家的门时,开门的大爷见是我们,开口便说,这么大的雷暴雨,就怕你们被堵在家里,逃出来了,这就好了!我们被引到一间较空的房间,架起了柴草,点起了火,烘烤被淋湿的衣服。后来大爷又端来热姜汤给我们喝,以抗风寒。也就是在这间草屋,铺上草席,我们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逃难逃进了土匪窝
头晚国民党保安队没有进村,大概是为暴风雨所阻,曹家岗的人也因此有好多未能逃出来,第二天一早才陆续离村。这是第二天同从村内来和祖父打招呼的人的谈论中得来的消息。
早餐吃得很晚,而且大爷特地做了摊饼,这是干粮。这里农家早餐不干重活是不会吃干粮的,让我们吃干粮,预示我们要远行。临行前我们才知道,是让我和云青到嫂嫂的娘家去。祖父送了我们一段路。拐向别的村子去了,由我们自己前去。
午饭以后,赶到了嫂嫂娘家,嫂嫂并没有逃回娘家,到了哪里也不知道。吃完饭已经是下午,嫂嫂父母很热情,问清了情况以后说,为了安全,晚上你俩和“大的”(他们的大儿子)到村北边的“稻场”上去睡,以免让人堵住了大门,跑不出去。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出了难题,他们得到的消息,土匪队伍晚上很可能流窜到这里,他们正在收拾东西,以应不测。这些,当时并未告诉我们。
晚上,我俩跟随“大的”到了他们家的稻场上。我们钻进了秫秸支起的“房屋”,睡在地上,和“大的”讲起了故事。我渐渐睡去,醒来时天已大亮。当我喊第一声时,云青厉声厉色地让我小声点,指指外面说,村里已经住进了土匪,不远处土匪已布置了岗哨,我们已经不能出去了。
这真叫逃难偏入土匪窝。云青和“大的”都比我年长、懂事,安慰我说,不要怕,只要我们不动弹,没有人会想到这里有人。昨晚土匪就是经过这里进村的,没有喊醒你,怕你害怕,现在只能等候看情况变化了。从秫秸秆的缝隙向东北方看去,200米外有一位带枪的岗哨在走来走去。稻场的南面有一间独立的小屋,住着一户人家,大门是关起来的,见不到人影,这家人是逃走了,还是不敢出来?走不出去,憋在这里,一分钟一分钟向前捱着。时间已近中午,我们滴水未进,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可以说是又渴、又饿、又烦、又急。突然,独立小屋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男人,后面跟着小狗,在门外收拾他家的杂物,两眼在观察四周的一切。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是我们叫二大爷的,从曹家岗搬到这里,他也认识我们。云青说他一个人先去看看,“大的”说,他出去合适,因为土匪在附近放了岗哨,他是本村人,住在自己家的场上合情合理。这样,他带着不无恐惧的紧张心情,一步步走进了二大爷的家门,远处的岗哨没有理会。当二大爷得知我们在稻场上时,他自己扛了一把叉子,来到场上,领着我们到了他的家。
进家以后二大爷就批评说,你们早该到这里来。“大的”说,因为大门紧闭,我们以为房内没有人了。还是云青比我们懂事,他说,我们来是会连累你们的。二大爷说,曹家岗的人,不说这些。他热情地吩附家人打洗脸水、倒热茶、做饭,就这样使我们安定了下来。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二大爷说,先别着急,土匪已经进驻了这里的几个村庄,不能贸然出去,看看情况再说。太阳偏西,从嫂嫂娘家的村里向这里走来了一个人,空着手未带武器,二大爷盯着看了一会儿说:“好了,有救了。来者叫曹三,曹家的人,按族中辈分,你们是兄弟,同辈人,他是个土匪小头头,托他帮忙,他不能不办。这样,你们就能离开这里了。”我们带着疑虑注视着来人,毕竟他是土匪,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土匪是什么样子呢,也有些害怕。曹三是来看望二大爷的,语言不多,也还和蔼,当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他说你们尽管离开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当我们迅速离开并到达董村时,嫂嫂的父母正站在高处向稻场方向张望,当他们辨认清楚来者确系我们三人后,压在心头的大石头落地了。他们解释说,昨晚土匪是从我们所在稻场的这个方向进村的,所以无法通知我们离开。当我们打听嫂嫂的消息时,他们才告诉我们,从曹家岗方向过来的行人说,国民党的保安队已经进了村里,看到几处在冒烟,是保安队放火烧房子,烧的谁家房子就说不清了。
我们为什么能顺利离开土匪窝,化险为夷?是二大爷的面子,还是土匪同我们家有什么交情?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早年乡间土匪的情况。
20世纪30年代,寿县农村的基本矛盾当然是源于封建的土地制度,代表封建地主的是县、区、乡的官僚、恶霸,他们无恶不作。连年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群众活不下去了,因而铤而走险,聚众为匪盗,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一次行动,往往占领数个村庄。这时的农村,三股势力在交错,一是县、区、乡的官僚和他们的保安队,这是统治者;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农会和游击队;再就是土匪队伍。共产党人尽力在做土匪的工作,联合他们,以求改造他们。但他们不和共产党沾边,原因是和共党来往,戴上了红帽子,国民党就死追猛打。国民党是把共产党作为其主要敌人的。这时的土匪一般来说也不会伤害我们,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是本乡本土人,情况熟悉,伤害了他们,必然要受到制裁。有时二者之间也会互通情报,搞点互相支持。我们这次能顺利离开匪窝的道理就是如此。
离家之后
1938年4月,我和云青离家奔赴延安。此后故居的一切情况都不是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许多具体情节是和母亲聊天时知道的。我们走后,故居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革命阶段,敌(日)、伪、顽、友、我各方在故居所经历的斗争,极其复杂、激烈、残酷,跌宕起伏,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我们的家庭、亲友,已经是血溅原野,家破人亡。故居已是残壁断垣,仅存的几间破漏草屋,还傲然屹立在园子上。就是这草屋在向世人宣告,三烈士故居还没有被摧毁,三烈士的家人没有被灭绝。
大郢孜不懂事的小孩往往说,园子上没有“带把儿的(指男的)”,只有女人。是的,男的死的死,逃的逃,幸存者战斗在革命需要的地方。只有女的在园子上坚持、挣扎、斗争,她们是母亲、小姑和孟家大姐,有时两位嫂嫂也在。孟家大姐,是大伯的女儿。小姑是母亲的女儿(养女),人们称母亲为老姑,称她为小姑,我们走后,母女相依为命,更艰苦,也更困难了。母亲说,你在家时(十年内战时期),那里虽然抄了家,但“跑反”还有个周旋余地,后来的“跑反”,已经无处可去了,跑日本鬼子的反,是所有人一起跑,还好一点,后来跑国民党的反,十分残酷,不是至亲骨肉,都不敢沾边了。(特约撰稿 曹云屏)
(作者为曹渊烈士之子,离休前曾任中共广州市委顾委副主任)(责编:汤宁 初审:孙继奎 终审:沈国冰)
特 别 声 明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寿县融媒体中心(寿县广播电视台)为寿县县域内唯一具有新闻采编、播出资质的媒体机构。寿县县域内,其他所有自媒体及商业媒体均不具备新闻采访、编辑、转载、发布等资质。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主管运营的媒体平台有寿县县委主办《寿州报》、FM101.2、FM105.9寿县人民广播电台,寿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寿县发布”、“寿县广播”微信公众号,@寿县发布微博,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寿县新闻网,寿县手机台APP,寿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是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县域官方主流媒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属媒体平台发布的所有信息,未经授权,禁止任何自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特此声明。
 “锯树留邻”有了新故...
“锯树留邻”有了新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