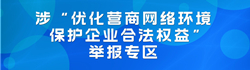双乡之间许洁诗歌怜悯转向
诗人许洁出生于安徽宿松县华亭镇五谷庙,2012年时从福建奔赴哑巴店履职,从此便选择哑巴店作为以后的栖居地,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其诗歌的精神坐标系。五谷庙作为其“生命意义上绝对性的故乡”,承载着血缘与宗族的原始印记;而哑巴店则是“地理转移和精神迁徙后的第二故乡”,是诗人通过自主选择建构的生存空间。这种双乡结构以一种动态基因融合,正像诗人自述的那样:“我把五谷庙的基因带到了哑巴店,又把哑巴店的基因带回到五谷庙,最后合成为现在的我”。
因此哑巴店不仅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场所,更成为其观察生命本质的“诗学实验室”。在《哑巴店的树》中,自然静物被赋予痛感:“池塘的绿也依次推开了表面的热情/此时的哑巴店,风和雨都歇了/落日一直保持着它的缄默”。这种拟人化描写并非修辞游戏,而是诗人将自我生命体验投射于外物的结果。当诗人在《在哑巴店》中写道“百年老店不见了,可哑巴还在”,这里的“哑巴”已超越具体人物,升华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所有进入这个村庄的人“都开始慢慢地学会:不是学会说话,而是学会不说话”。
梁小斌在诗集序言中敏锐指出许洁诗歌的核心矛盾:“论及许洁,必须冒出一个关键词:怜悯。在哑巴店的许洁,到底是‘铁蒺藜’占上风还是‘怜悯’占上风?”这一悖论恰是《哑巴店》的诗学张力。诗人早期倾向以“铁蒺藜”式的尖锐意象解构乡村浪漫化叙事,如《我宁愿落叶是一枚尖锐的铁蒺藜》中,落叶被赋予抗争性:“我宁愿它们叮叮当当,伤痕累累/我宁愿它们能在林荫道上/认真拦住我们的路”。这种将柔脆之物刚化的逆向想象,实则是对“生命尊严的强力捍卫”——诗人要求被漠视的个体发出声响,哪怕这声响源于痛苦:“能把一半的尖叫声分给它们”。
随着诗艺成熟,诗人逐渐实现从“铁蒺藜”向“怜悯”的诗学转向,或者说“怜悯”一直是诗人创作的基本底色。据其自述,曾在雷声大作时打破瓦罐,发现内藏“米粒和铁蒺藜的残骸”,当将碎片重新合拢,“间隙里逐渐地爬出了两个字:怜悯”。从“铁蒺藜”向“怜悯”转向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 第一层面便是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在《雷声让我想到哑巴店》中,他以冷静的笔触刻画“秋天的雷”和“守林人荒凉的酒盅”,聚焦这些被生活边缘化的存在。这种关怀并非煽情,而是像显微镜般精确呈现“哐当哐当挖掘不尽的羁旅”,揭示乡土日常中潜藏的伤痛与失序,其悲悯根植于对具体生存困境的体察。
其二,这种关怀也扩展为对自然生态的悲悯。《一棵病树》中,“拉起警戒线”的灰蜘蛛围绕着挣扎的病树,这不仅是单一植物的病态,更象征整个自然生态所受的创伤。蛛网是自然的自我防御,也是对工业化侵蚀的无声抗议。破碎阳光下的皱巴树干,宛如一部沉默的自然哀伤史,诗人借此表达对受创环境的深切同情。
最终指向,怜悯升华为对乡土文化根基的追寻与救赎。《在五谷庙》里,“跪等金光的母亲”成为核心意象。她虔诚跪拜的身影与庙外谦卑的稻穗相叠印,融合了信仰的虔诚与农耕的辛劳。诗人暗示,怜悯的终极意义在于对“原乡”的呼唤与守护。母亲期盼的那束光,不仅穿透庙宇的昏暗,更试图在现代性变迁的迷雾中,照亮那可能迷失的乡土精神内核。
当诗人宣称“我的诗歌基本上都来自我的生活,来自我成长的环境,来自我的家乡”,他揭示的不仅是创作发生学,更是诗与存在本质的同一性。在今天,《哑巴店》如同稻浪中的麦芒,以异质性的刺痛守护精神的多样性。那些“倾斜的花香”(《哑巴店的春天》)终将在诗行中获得扶正,而洄游于双乡之间的诗人,已然在“间隙”中筑起抵抗遗忘的语言。
特 别 声 明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寿县融媒体中心(寿县广播电视台)为寿县县域内唯一具有新闻采编、播出资质的媒体机构。寿县县域内,其他所有自媒体及商业媒体均不具备新闻采访、编辑、转载、发布等资质。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主管运营的媒体平台有寿县县委主办《寿州报》、FM101.2、FM105.9寿县人民广播电台,寿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寿县发布”、“寿县广播”微信公众号,@寿县发布微博,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寿县新闻网,寿县手机台APP,寿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是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县域官方主流媒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属媒体平台发布的所有信息,未经授权,禁止任何自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特此声明。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