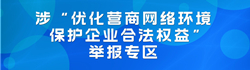吃在寿春
寿春城东大街的面条馆里热气腾腾,天已经很冷了,大清早,从后窗户看过去,里进的那间屋顶上已经积雪很厚,屋檐下还挂着长长的冰凌,几个做瓦工活的常客已经喝下了几瓶浑酒,端着洒上芫荽和蒜的面条碗,用筷子挑起来然后拖到他们嘴里,其实“吃在寿春”,这句话应该作这番解释,一是城里人多,他们需要吃饭,这是一个吃饭的城池,二是在寿春吃饭确实是有些特殊,虽然同在一个城里,因为饮食习惯的小小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女士和孩子们可以在棋盘街9号吃鸡蛋汤,老夫妻俩手脚麻溜,在沸水里撒上白白的蛋花儿,像雨后初晴的天空上有淡淡的云彩。盛上一碗,搁上芫荽、浇上麻油、再撒上点胡椒,两块钱一碗来!蛋花细细的,喂给小孩吃,大小松软正好。小小孩子坐在小椅子上,两只小手握着小拳头放在膝盖上,如果是冬天大人哈着热气,看着孩子们吃下去,于是这一天就有了精气神。寿春城早点生意哪哪都好,因此上就没有给顾客太多殷勤的感觉,寿春没有“阿庆嫂”,“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没有人这么说,吃饭生意很少招呼,城里人多,只要对口味,吃的人总是有的。不愁没顾客。

像丁家馄饨、北方水饺、如意水饺这都是寿春城的老字号了,在这里吃饭很有意思,要几碗水饺或馄饨,几笼包子,然后在那里要几样家常小菜,例如炒胡萝卜丝儿、咸鹅爪子,再远些说,要几大杯寿春“专供”的枣子泡成的酒,于是弟兄几个就喝上了,在寿春一喝上酒,其食相就显得不那么严肃,“阿(相当于俺)哥爷,你照这样讲话阿就没的讲了,阿跟你讲,东菜园子那块地皮是阿家的。”然后嘴里“嗡嗡”的,反正这枣子酒将满脑子抻得很绵软,店家用黑黑的毛巾不时揩拭桌面,然后再一句,“再上一碗水饺。”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在外面吃饭的,他们的父母在家都是挺担心的,几个青皮小生不上进,整天就知道喝酒、抽烟,又没个正经事做,干起活来懒懒散散,喝起酒来浑身是胆。喝过酒再在外面惹事,在箭道巷、北过驿巷打架,欺负人家学生,这是父母最担心的,再这样搞下去,改天再进了北山看守所,想也不敢想,寿春城的父母本分的多,父母为子女操着心,不听话的孩子是让大人焦心呀。
来品。寿春的葱举城少不了食用,洪水期间,剩下没淹了的一小块地里烂歪歪的葱可能是养育城池味觉的一大佐料了,揎去烂叶,露出蝉翼一样的葱皮,“(美女)手如削葱根”当是谓也。将它们横切开几瓣,再拦腰这么切成细丁,撒在和好的面饼上,再卷成团使劲地揉搓,再用擀面杖抻开,放在平底锅上,油炸,甫成,此即寿春油馍也。我们品味过那味道,如同沈从文吃了汪曾祺做的鱼那样,说一句,“真好吃”。
做油馍的早上四点钟起床,起火添柴,油烟四布,食客们坐在墙角,在郝家巷、将爷巷,电话杆上的嗽叭播放着“小青姐姐讲故事”,积水未散时候,双眼惺忪作起了“屠门大嚼”。五点多钟就有人坐在那儿等着了,就像一位货主等着后堂师傅提供饮食一样,寿春男人有着那种“城墙根”的习性,虽不是炊金馔玉,但也有些“割不正不食”的穷讲究,吃过了来一句,“好吃还是寿春啊。”然后拎着玻璃茶杯东走走,西走走,到孔庙看人打牌,一看就是一个上午,这就捱过一日,第二天五点准时又来吃油馍,摊主就将切好油馍递上去,反正食量都有准谱的,谈起话来,也只是“今天柴禾有些个潮”,“萨达姆上吊了”等等。
余音先生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吃在寿春并不是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的就是那个味,寿春嗜咸重味,在酸甜苦辣中找到一种平衡,扩大来说,似乎在历史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准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由“吃”而生发来的,余音在《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创办风云》一书中描写了孙状元的一段“吃”。
1898年6月9日傍晚,孙家鼐一件件脱去被汗水浸透的官帽、官服和官靴,坐在太师椅上,接过冷面,大口吃起来,这冷面是用家乡寿州的老办法料理的。先煮熟,捞出来用井水冷却,半个时辰后捞出来,空干水,再添上葱花、剁椒、香菜,浇上香油、酱油。王氏见丈夫(吃得)头不抬眼不睁,无话找话地问:“老爷,味道可照?”孙家鼐点点头,用家乡话应道:“乖乖,真好吃。”
又一个“真好吃”。我不知道这段话是不是余音先生杜撰的,但我想对寿春小吃的回忆也许是包括孙状元和余先生在内的许多游子的共识了。对晚年的孙状元来说,这冷面肯定比安徽会馆里的美味珍馐好吃,这话是不差的。当了大官,海吃山喝真是太受罪,孙状元的侄子孙毓筠当上安徽军政府都督时说了一番话:“我在安徽,实在没有办法,各处的军官,都是拥兵自大,不买我的账,各县行政官不交钱粮,财政官不交税收,我是一文莫名,人家向我要钱,我到哪里去生财呢?都督府成了寿州会馆,每顿要开几十桌饭,吃不合口味,就发脾气大骂,这岂不是活受罪吗?”这些上饭桌的,我们无证据断定就是在寿春喝枣子酒啃猪蹄的主儿,果若如此,那就是吃出负担和祸事来了。
最近一次吃的事件,在东大街城隍庙附近,两个老头相遇了,寿春城的老头儿大夏天里穿着白色的背心,露出松松垮垮的大膀子和胸脯肉来。有人说,“寿春宜居”,“寿春宜养老”,这话就要在街边槐阴下相逢一笑而得见,甲老头对打西向东来的乙老头说,“一碗凉面下肚了?”在寿春,人们之间就是这样知根知底,什么样的喜好,什么的吃相,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乙老头说,“不对,俺吃了一碗炒面。”炒面,这可不是寿春的小吃儿,虽然做法要繁琐一点,但价格不菲,商家也乐意去经营,学校里,学生们下了学,就挤在炒面摊前,炒得一碗面,夹一双一次性筷子,托着泡沫饭盒走着就吃了,类似于此的烧烤也一样在热闹地儿冒着缭绕的青烟,寿春当地的小刀面等饮食除了清晨时分,剩余的时光都寂寂于巷陌中了,唯有煤球炉还冒着残留的热气。
最近一次关于寿春吃的问答,是我与同学之间展开的,我问,“徽州早餐有什么好吃的?”,他说,“稀饭、米糕、鸡蛋,豆浆,徽州煎饼、锅贴饺,大烧饼。”我说,“你吃过寿春的油馍吗?”他说,“类似于陕西泡馍吗?”我听了很无语,心里想,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呢。他说,“我吃过寿春‘大救驾’。”我突然感觉到一阵阵的激动和振奋,我问,“感觉怎么样?”他说,“味道挺不错的,就是不好看。”我又是一阵无语,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的感觉与我同学的感觉正好相反,大救驾味道不怎么样,样子倒是很美的,层层叠叠,蜿蜒盘结中心。是我看到的最美的食品,因为它是古食品,并且与一段决定江山社稷的故事有关。怎么能说不好看呢。
特 别 声 明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寿县融媒体中心(寿县广播电视台)为寿县县域内唯一具有新闻采编、播出资质的媒体机构。寿县县域内,其他所有自媒体及商业媒体均不具备新闻采访、编辑、转载、发布等资质。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主管运营的媒体平台有寿县县委主办《寿州报》、FM101.2、FM105.9寿县人民广播电台,寿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寿县发布”、“寿县广播”微信公众号,@寿县发布微博,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寿县新闻网,寿县手机台APP,寿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是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县域官方主流媒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属媒体平台发布的所有信息,未经授权,禁止任何自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特此声明。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