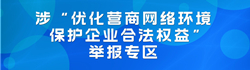长青
我一生工作过的地方不少,教过书的学校也有三四所,唯工作仅四年的长青中学在我的心里占据的位置最大。或许是因她,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许是因她,我才当上了教师,走上了从教的路。尽管那是个偶然的瞬间,是间接的,但记忆却极为深刻。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严寒而干燥的冬天,我和下放所在生产队的一群小青年被派到三觉桥湾与谢埠花果的交界处修建花果水库。四十多天时间里,每日的工作就是抬土。一根竹杠一个大大的柳条筐,从远处的库底取土,一趟趟一筐筐地往坝坡上抬。抬着满满的一筐土,上坡,步步艰难。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才能收工,累得晚上睡觉时浑身酸痛。好在那时年轻,休息一夜便好,虽又累又苦,但整个人精气神还算很足。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这所紧挨着库北岸的寿县长青中学;也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走进了长青中学。
记得那天晚饭后,天很冷,月很亮,一阵阵歌声伴着悠扬的手风琴声随风越过坝南堤,飘到了我们所住的库南的自建的庵棚里。我和几个小伙伴按耐不住,顺着歌声,一路朝北,越过漫长的库底,朝着雪亮的灯光寻了过去。翻过干涸的围沟,便看见了一排排草顶土墙抹角头的房子,原来这里就是长青中学,这些房子便是教室。可能是周末,几个教室里上自习的学生并不多,很安静。最东头的一个教室里,雪白的汽灯光下,一位年轻帅气的男教师正指导着一群男女学生排练歌舞;一位短发的漂亮的女教师在拉着手风琴。歌声琴声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看着教室里老师和学生,看着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看到他们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勾起了我对以往的的校园生活的美好的回忆,我心里好一阵酸楚,我很难过。好久了,没有到过学校了,没有见过教室了,我好羡慕他们啊。
或许正对应着我当时艰难的处境,因此那时、那地、那景着实深深地刺激了我,也激励了我,鞭策了我,鼓舞了我。在窗外,我暗自发誓,我要读书,我要和多舛的命运抗争。自那日起,我奋发图强,不懈地坚持自学,几年后,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教师梦,走进了神圣的校园。
正因如此,长青中学,长青中学教室窗外的这一幕,才会令我终生难忘。
我决定去长青看看。
重阳节的下午,迎着西挂的夕阳,我独自驾车前往。秋阳暖暖,秋风习习,路上,但见道两旁无际的稻海荡漾着金波,一台台收割机狂吼着穿梭其间,今秋淫雨成灾,眼前却呈现出如此丰收景象,一时间心情大好。
在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面的花果水库大坝上,车停了下来。到长青来,得先来花果水库,一来,这样回程不绕路,二来,我想看看大坝。
站在坝顶举目西望,见库面波光粼粼,一群群野鸭在水中嬉戏,看远处水天相接,夕阳下,水面红光闪烁,景象甚美。这水库比当年大多了,水面比当年宽阔多了。低头看看脚下的雄伟的大坝,我竟有些许自豪:这大坝的筑建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这巨龙般的大坝上曾留下过我青春的足迹,洒下过我辛劳的汗水啊!
步行到学校,见大门敞开着。关停后,老师们都调走了,学校里已无人居住。可能是供给村民们在校园里水泥路面晒稻子的原因,大门没有上锁。
伫立在大门口,看着空荡荡的校园,我的情绪瞬间低落下来,一时间思绪万千。
长青中学曾是一所完中,1965年建校。1968年,8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这里。一片荒地,几栋教室,无图书,无教具,无寝室,吃水靠挖的土井里浸的一点和着小蝌蚪的浑浊的水。艰苦的条件并没能将这批年轻人打倒。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当地的教职员工一起,打土坯、垒住房、挖围沟、整操场、搞绿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年复一年,努力奋斗,不仅把学校打造成了花园般的整洁美好,且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优秀的初高中毕业生,为祖国为安徽为寿县的经济建设、教育事业的发展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宝贵的人才,创造了长青中学的第一次辉煌。
德高望重的赵涤新老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和爱人朱国莹老师一起在这里奋斗了8年,直至学校高中部撤销。尽管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尽管他夫妇后来调往寿县师范乃至马鞍山任教,直至退休,老先生始终心系长青,至今仍是“长青中学教师微信群”里最活跃的一位。赵老先生和所有的长青的教师一样,心系着教育教学,对所有的付出无怨无悔。正如他说过的:只要你的青春在这里闪过光,只要你在这里努力过,在这里奋斗过,那就够了。
许是天道酬勤,亦或造化弄人,自那日从花果水库第一次走进长青,怎么也没想到,十年后,我竟做为长青中学第五任校长调往这里任职。总记得区委领导的那句“希望你为长青中学改变面貌”的嘱咐,四年里,我殚精竭虑,勤勉工作,未敢懈怠,遗憾的是我并未能让长青彻底改变面貌。好在一任接着一任干,终在第六任校长刘学辉任上,长青中学迎来了她的再次荣光。学校逐渐发展到拥有十八个教学班,1200多名学生的一所中等规模的乡村中学。宏伟的教学楼、气派的大门建了起来,平整的贯穿整个校园的水泥路修了起来,教师们住上了宽敞的砖瓦房。长青中学的升学率走在了区、镇前列,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送出了像全国劳动模范张士家,火箭军全军学习标兵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侯长岭等一大批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科研、教育人才,让这所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老校迎来了她的第二次辉煌。
青春会逝去,繁华会落幕,所有的事物都有荣衰兴亡。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村的青年人大都走了出去,孩子们都随着父母去了城里,农村适龄儿童骤减,农村中小学开始了大规模的关停并转,长青中学也和许多学校一样,撤并了。一所有着光辉灿烂历史的60年老校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缓缓地关上了她神圣的大门。
寂寥的校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教学楼孤独地高耸着,教室里再也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安静得让人窒息。我漫步在空荡荡的杂草丛生的操场上,又轻轻地走进空空的教室,无法言喻的怅然、失落感在我的心中肆意蔓延。
站在大门旁,我抚摸着依然闪着光的大门外墙上镶嵌着的“寿县长青中学”的几个钛金大字,忽然就想到了“母校”这个词。人们常把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这一刻,我觉得这个词好亲切,好贴切。哺育我们成长,培育我们成才的学校不就像是母亲吗?面对着门墙,我的眼里仿佛浮现出一位年迈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影像。这面墙,这大字,多像一位慈祥的老母亲正端坐在老家的门前,守着老屋,守着门,静静地眺望着远方。她在想念着她的儿女,她在倾听着儿女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声声问候,倾听着从天南地北发来的莘莘学子们为祖国建设建立功勋的消息。
母亲在,学校在,她铭记在所有长青学子们的心里,也镌刻在那些为了她的荣光而无私奉献过的所有老师们的心里!
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我该离开了,我该回去了,虽依依不舍。
上了车,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这座我曾挥洒过汗水、倾注过心血、留下青春印迹的校园,虽被光阴磨损,却依然在我的记忆里长青。
特 别 声 明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寿县融媒体中心(寿县广播电视台)为寿县县域内唯一具有新闻采编、播出资质的媒体机构。寿县县域内,其他所有自媒体及商业媒体均不具备新闻采访、编辑、转载、发布等资质。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主管运营的媒体平台有寿县县委主办《寿州报》、FM101.2、FM105.9寿县人民广播电台,寿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寿县发布”、“寿县广播”微信公众号,@寿县发布微博,寿县人民政府网站、寿县新闻网,寿县手机台APP,寿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是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的县域官方主流媒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寿县融媒体中心所属媒体平台发布的所有信息,未经授权,禁止任何自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特此声明。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
寿县:走马古城寻“蛇...